
这部小说的京东购买链接:
我新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本小说将在那里连载,欢迎扫码关注,非常感谢:

这个链接,有更详细的介绍,众筹预告视频,及作品定位介绍视频,敬请观赏:
作者中新经纬的专访视频:
同时,也在采取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的众筹模式,大家一起来推进《青春做伴》的影视改编项目,可以当做一个好玩的创业项目。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能力,及资源:影视投资人,影视公司,编剧,导演,演员,媒体人,地推,营销,宣发,品牌,公关,文案,等等。大家以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入股众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贡献,拿到相应的股份,最终通过股份,拿到更高的回报。主要演员也将基本通过海选方式产生。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加我微信leejcheng。
总目录页:http://chenglijian.blog.caixin.com/archives/167104
第三章
No matter how hard you prepare for it, you are never ready. (不论你怎么准备,你永远准备不好。)
我从来没有这样怕一个约会过。
整整一周,我一直在做思想准备,我想着:“一定要想好一切该做的行动,该说的话,该安排的节目,一切可能的意外,以及所有应对的措施。”
“应该送她一束玫瑰吧?”我接着想,“如果在复旦就事先买好了,带过去会不会坏了呢?嗯,记得馨儿学校那边有一家花店的,就在那儿买一束送给她。她喜欢黄玫瑰,不过,这次,应该是红的吧?好,就定下是红玫瑰了。然后,我该不该说:‘我爱你。’呢?”
我想着想着,不由得笑着摇摇头:“‘我爱你’,好象实在是太肉麻了!要不然,就用英文说I love you 吧,好象自然一点儿。一进门,躲在玫瑰后面就说,应该是可以说得出口的。”
我点点头,接着想下去:“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可以去吃快餐,麦当劳或者是肯德鸡。吃完了,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当然,现在象以前和以后一样,不会有什么值得看的好电影,不过,可以两个人呆在一起。我的手应该可以搭在她的椅子背上,然后去挽她的肩。黑暗中,我们不会太尴尬。电影看完了呢,我可以揽着她一起去黄浦江漫步,在江边,任清凉的秋风吹着我们......”
一直到前一天晚上,我都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计划得很好。
可是,早上一醒来,我却又开始怕得不得了。我实在怕面对馨儿,怕同她相处得不好,不得体,更怕让她失望。
一直拖到下午四点多,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能再拖了,这才出发。
一路上,我骑得慢慢腾腾的,头也有点儿昏昏沉沉的。离馨儿的学校越近,我也骑得越慢。
咣当一声响,我的车子在一道小沟上颠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头脑也一下子清醒了点儿,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周末,谈恋爱的学生那么多,人人都买花,一定会把整个花店堵得水泄不通的,我得赶紧去。”
我加快了速度,先骑往花店。快到了,远远望过去,没想到却是没有什么人。我暗暗高兴,快蹬了几步,冲过去,跳下车,冲进花店,兴冲冲地大叫一声:“老板,来一打红玫瑰!”
一个年轻人在柜台后面象是看一个外星人似的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看得我直发毛。
我低下头,喘着气,压低了声音说:“您给来一打红玫瑰。”
他还是没有说话。
我抬起头,看了看他。
他这才笑着说:“第一次追女生吧?”
我有点着急,脱口而出:“关你什么事儿?卖你的花儿不就得了。”说完了,我是后悔不已。惹了他,一怒之下,不卖我花儿了,我找谁去呀?
他倒是没生气,还是笑眯眯地说:“别生气啊。我们这儿,大学生随便是个人就在谈恋爱,你知道玫瑰都得提前几天跟店里订吗?一般是这周约会完了,马上订下周的。就算是刚吵了架,想用玫瑰和好的,也得一开门就早早地来店里买啊。象你这么晚的,我上哪儿给您找花儿去呢?”
我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好声好气地说:“大哥,您还真看得准。我这还真是第一次。您也知道第一次的重要性,您看看,能不能帮帮忙?”
“不是我不帮,我倒是想帮呢。有生意,又能帮人,谁不乐意呢?”他摇摇头说,“我是真的没有了,这个礼拜又偏偏是新学期刚开学,重逢的,新聚的,生意特好,我早上十一二点钟就卖光了。”
“真的没了?!”我还存着一线希望,“哪怕就几枝呢?”
“我蒙你干吗?”他说。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掉转头,走出去。
“唉,等等。”他叫住我。
我充满希望地回转头看着他,问:“是不是......”
“不是。”老板笑着摇摇头,“只是提醒你,要不要订下周末的花?”
我也笑了,一边说着,一边走回去:“好吧。您可真会做生意。”
我在他的预订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刚转过头要走。
老板又叫住我:“嗨,别急着走,还没付订金哪!”
我又忍不住笑了,说:“我算是服了您的生意经了。要多少?”
“花价的一半。另一半取花的时候再付。”他说。
我一边取钱,一边笑着说:“您是不是特盼着我下个礼拜不来?白收了我的订金,您又不愁再卖出去。”
他也笑了。
看着他在那本又脏又乱的预订本子上到处找我的名字,找了半天才找到,然后草草地写下订金已付。我突然心中一动,想起来以前在中学帮教育局管理网络的事儿,当时总想也做做软件,现在,似乎是个机会。我问他:“这么乱的预订本子,您会不会常出个错什么的?”
“当然,经常有。如果倒霉,碰到一个横的主儿,又要的是特别的花,我们忘了订。或者是我们自己店里的人写在不同的地方, 订货订漏了。吵顿架是常有的事,弄不好,还能打起来。”他叹口气说。
我忙说:“我是学电脑的,要不要我帮你设计一个电脑系统?先可以把订花管起来,然后可以管帐,管工资,管货存.......”
“好是好。我也听说电脑挺厉害的。不过,好象电脑很贵吧?再说,你要收多少钱做系统呢?”他蛮感兴趣的。
我想起来我们系里正在淘汰一批旧的IBM AT 的机器,就说:“没准我能搞到便宜的机器。是我们计算机系里换代下来的。几千块钱就可以了。在市面上,也不算太落后。”
没想到他马上说:“噢,我还以为得好几万块呢。这钱我投了。人工费呢?”
我犹豫了一下,心中也没谱。以前,管网络的时候是两块钱一小时。我想了想,编程应该累得多,加一倍多吧。于是,我抬起头,试探着说:“五块钱一小时。”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搞完呢?”他又问。
“一星期我也就能工作二十个小时,可能得一两个月吧。”我比较有把握地说。“不过,这只是订花的部分,其他的部分,象管帐之类的可复杂多了。”
他马上说:“那好,就这么说定了。”
看着他答应得那么爽快,我又有一点儿后悔要得太少了。我的商业头脑实在是太差了。
他看着我的样子,笑着说:“我再加你点儿,每个周末我再加送你一束免费的红玫瑰。”
我也笑了,说:“好吧。反正跟您这儿,我怎么着也得吃亏。”
然后,我看了一眼表,大叫:“都快六点了!我得走了!”
“你再等等。”他又叫住我,自己走进店后面。
我不耐烦地等着他,不停地看着表。
他匆匆地走出来,手里捧了一束美极了的红玫瑰。
我大叫:“不是没货了吗?!”
他笑着说:“留给我女朋友的。便宜你小子了。今晚上我少不了要挨一顿骂。”
我一把夺过花,大叫一声:“不好意思。谢了啊!”转身夺路而跑,生怕他改变了主意。
我飞快地骑到馨儿的宿舍,呼哧带喘地跑上楼,到了馨儿的寝室,还没有敲门,馨儿已经打开了门。
我递上玫瑰,说:“不好意思,来晚了。”
馨儿欣喜地接过去,轻声说:“谢谢你的花,真的好美。”
“那是。”我有点儿得意洋洋地说,“是最棒的。花店老板留给他女朋友的,让给我了。”
馨儿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问:“怎么回事儿呢?”
我兴冲冲地说:“我一直想着要买玫瑰送给你,谁知道下午冲到花店,老板说周末的玫瑰早就被买光了。气得我直吐血。老板还特别会做生意,一个劲儿地劝我预订下个周末的花,还要预收一半的订金。我一看他破破烂烂的预订本子,马上计上心来,劝他搞个电脑管理系统。我可以半工半读帮他编程。”
“他店里有电脑吗?”馨儿问。
“你说巧不巧,我们系里正好更新换代一批IBM AT的旧电脑,我可以帮他买一台。嗯,对了,还可以再赚一点儿差价。”我心里想着,这点儿差价可以补回一点儿编程要价低的损失,越发得意地说,“编程费,他一口答应一个小时五块钱,应该说低了点儿,不过,也还凑合了。另外,还有一个周末一束免费的玫瑰。这个周末,他还真的没货了,只好把给他女朋友的那一束送给我了。怎么样,干得漂亮吧?”
馨儿微笑着,点点头。
我得意得几乎都有点飘起来了。
馨儿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花放在桌子上,一边对我说:“你坐一下,等我一会儿。”然后,她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我忙说:“找什么呢?我帮你。”
她手在身后挥了挥,一边接着找,一边说:“不用了。你不知道在哪儿的。”
我只好四处找地方坐下。我还是第一次真正地进女生宿舍,和我们男生宿舍相比,真的是太整洁了,坐在哪儿都怕给搞脏了。
馨儿看见我局促不安的样子,笑着帮我搬了把椅子。
我也笑了,故意直直地坐在上面,把双手叠在膝盖上,头低着,目不斜视地看着脚尖。
馨儿大笑着,推了我一把,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一边跑出门外,一边对我说:“再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听着馨儿开心的笑声,我一怔,问自己,上一次让馨儿这样开心地笑,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
馨儿很快就手里捧着一个大的玻璃的果珍瓶子,里面盛满了水。她把瓶子放在窗台上,小心地把那束玫瑰插进去,又细心地把花一枝一枝地整好,然后,才把瓶子转了转,向窗台的里面推了推,让花向着太阳。
那一刻,阳光洒满了她的全身,柔和而温暖。我的心里感动极了,我感到我的眼中已经是潮潮的了,我很想冲过去,拥紧她,贴在她的耳边,轻声说I love you。
这个时候,馨儿转过身,她的眼睛里也是亮晶晶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馨儿对我说的话:“你可以还象以前一样对我吗?”
我又挂起了象以前一样的笑脸,故意大笑着,大声说:“这么大张旗鼓的啊?”
馨儿一怔,也马上笑着说:“你也知道的,我喜欢花。可惜没有花瓶。明天再买吧。好吧,等得不耐烦了吧?我们出发吧?有什么节目?”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甚至是最好的机会。我只知道我很后悔,很难过。我使劲地摇摇头,努力笑着说:“本来要去看电影的,不过,花店老板一磨蹭,你一磨蹭,可能来不及了。先去吃饭吧,民以食为天,我还真的饿了。”
“嗯。”馨儿应着。
“去哪儿呢?”我一边走着,一边有点夸张地说,“可不能太贵的地方,我可是已经被吃穷了。打工的钱还没挣到,老爸给的钱已经花光。”
馨儿笑了笑说:“不是说好了吗,该我请了?”
我摇着头说:“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花女朋友的钱,太丢份。”
馨儿笑着说:“好了,好了。我 们去吃学校的食堂。行了吧?”
我们一起跑到食堂。
一个大师傅正在收拾炊具。看见我们赶过来,很热心地说:“学生饭已经卖完了。不过,楼上有小炒卖。”
“要等多久?”我问。
“挺快的。”大师傅说。
我看了看馨儿,说:“既来之则安之吧?”
馨儿点点头。
我们两个人爬上楼,这才暗暗叫苦。
楼上排满了人,大多是情侣们。
我心里想:“小炒是现叫现炒,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没想到很快就到了我们,一抬头,发现刚才楼下的那位大师傅已经跑上来忙着收钱了。我和馨儿笑着对望了一眼。
“嗨,快点儿说,要什么菜。要是没想好,就先让到一边儿,让后面的人先点。”大师傅催着我们。
“想好了,想好了。”我急忙说:“一个鱼香肉丝,一个蒜茸豆苗。”
“好,下一位。”他飞快地记下来,马上抬起头来喊下一位。
我们让到一边。菜是出人意料地做得快。我们两个人坐下来,一尝第一口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快:菜和米都没洗干净,都是土和小石头,而且没怎么熟就起锅了。
我笑了笑说:“难怪那位大师傅说小炒挺快的。这么做菜是快了,可怎么吃啊。”
馨儿也笑了:“肉没熟,可真的不能吃。吃菜吧,没熟就当是吃沙拉吧。”
“也不知道是吃菜呢,还是吃观音土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跟这儿忆苦思甜呢。”我一本正经地说。
馨儿扑嗤一声笑出声来。
旁边一个男生也笑着说:“哈。你这话够损的。不过,食堂也真够宰人的。一到周末就早早地停卖学生饭,急着卖小炒。”
另外一个男生插进话来:“总比外面的小饭馆好点儿,一到周末就涨价,宰我们这些穷学生。饭一样的难吃。这儿,难吃是难吃,起码便宜点儿。”
他的声音大了点儿,他的女朋友瞪了他一眼,他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说话了。
我和馨儿也笑着,随便吃了点饭,只吃了个半饱就实在咽不下去了。
我抬起头,可怜兮兮地看着馨儿说:“不吃了,行吗?”
馨儿也忍住笑,说:“不许浪费粮食,不许浪费人民的血汗。”
我笑着说:“不是我们浪费,是做这菜的人浪费。求求你了。”
馨儿也忍不住了,笑出声来说:“好吧。”
我们俩笑着,从食堂里跑出来。
食堂外面,天已经黑了。笑了一会儿,我又有一点儿犯愁,下一步该干什么呢?看电影,八点多了,八点场已经误了,午夜场又还太早。
我一拍脑袋,突然想起来我计划好的下一个节目不是去黄浦江吗?提前不就行了?!
我暗骂自己笨,忙问馨儿“嗯,对了。馨儿,我们到黄浦江边上去走一走吧?”
“你确定要去吗?”馨儿看着我,迟疑了一下,问我。
“去吧。江边漫步,多浪漫。”我坚持着说。
“好吧。”馨儿偷偷地笑了笑。
“What? Your laugh looks pretty dubious. (为什么,你怎么笑得那么怪?)。”我调了句刚跟外教老师学到的洋文。
“没什么啦。走吧。”馨儿努力收起笑容,对我说。
我们骑上车。没想到那么短一段路,还真挺累人的。主要是一路上尽是圆圆的拱桥,上坡好陡,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才能骑上去,好几次,快到桥顶了,实在蹬不动了,只好跳下来,推着车爬上去。本来,下坡可以好好地享受享受,但是下面人和车子太多,而且,坡也实在太陡,我们只好不停地煞车。
好不容易快到了,我好象闻到什么味道。好象是一股臭味,越来越浓。我捂了捂鼻子,真的是令人窒息。我侧头看了看馨儿,她的嘴鼓鼓的,憋着气,实在忍不住了,才用嘴呼吸一口气,然后又憋起来。
我长喘了一口气,才问她:“这什么味儿啊?”
馨儿摇摇头,指着自己正憋着气的鼓嘴。向前骑着。
又下了一座桥,前面是一条挺宽阔的江。
馨儿跳下车,向我招了招手,说了声:“到啦!”然后,马上用手捏住鼻子,拼命用嘴呼吸了几口。脸上却笑眯眯的。
“哈!臭味是江里来的。”我看了看笑得怪怪的馨儿,恍然大悟,“原来,你早就知道。”
“哈,哈。还江边浪漫呢。”馨儿一边笑着,一边捂着鼻子说, “宿舍里的上海人整天都在聊黄浦江多臭多脏,整天抱怨上海市上交国家的税收太多,自己没钱治理黄浦江。”
“好啊,你看我的笑话。反正你也在这儿,咱们就一起浪漫,浪漫吧。”我也赶紧捂着鼻子说。
“好,啊。”馨儿捂着鼻子,一边用口呼吸着,断断续续地说,“看,谁,坚持,得久。”
我没说话,笑着点点头。一只手捏着鼻子,一只手推着车,沿着江边慢慢地艰难地“浪漫”着,馨儿也龇牙咧嘴地“痛苦”地跟着我。
没过多一会儿,我把车支起来,举起双手,刚要说:“我投降。”回头一看,突然发现馨儿也刚摇摇头,好象要放弃的样子,急忙咽下自己要说的话。
哪知道馨儿也止住自己的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只好说:“我认输了。咱们甭这么自己折磨自己了。”
馨儿也大笑着说:“太谢谢你了。我实在是也不行了。要不,就算是平手吧。”
大笑声中,也许是我忘了憋气,或者是刚才憋得太久了,我的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真的是可怕,那一股经年累月,浓浓的,发过酵,浓缩过,塞在你鼻孔处的,令人窒息的臭味。我大叫一声:“快撤!”跳上车,和馨儿夺路而逃。
骑了好久,已经离江边远了。我还是觉得那股臭味一直不去,好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缠着你,追着你。
我一边喘着气骑着车,一边侧着头看了看馨儿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味道好象是蛆似的,附在我们身上了。”
馨儿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你就少说几句吧?恶心死了。都是你,要去什么黄浦江。”
“是啊,有人不是明明知道,可是非要看我的笑话,结果,自己也栽进去了。”我笑呵呵地说。
馨儿也忍不住了,笑着说:“唉,真的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不过,我也没想到,臭得这么吓人。”
这时候,我们上了一个大桥。我累得不行了,忙说:“歇一会儿吧。”
馨儿点点头,我们停下来。
回首望过去,黄浦江边灯火如昼,映着点点的星光,和着远远的间歇的轮船的汽笛声,如果不是那不雅的味道,真的还是很美的。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我还计划着,江边漫步,欣赏夜景呢。真够劲儿的。”
馨儿顽皮地笑了笑,做了个鬼脸,没有说话。
我的心一动,急忙岔开话题,指点江山似的指着江边密密麻麻的破烂的小平房,笑着说:“住在那儿,可真够劲儿的。不过,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上海人都这么厉害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住在这种味道里,真的是苦了心志了。”
馨儿笑着,拉着我说:“你别损了。小心有人听见了,揍你一顿。”
我也笑了,说:“这我可听说了,上海的男生,骂人骂得凶,可是,从来就君子动口不敢动手。”
馨儿也笑着说:“嗯,有此一说。可我又听说,上海的女生可是又打又骂的。”
我一愣。
馨儿看着我发愣的样子,一笑转身,骑上车,说:“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我还想早一点儿冲个热水澡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又一动。我急忙正了正自己的心神,骑车追上馨儿。
到了馨儿的学校,正好是快要熄灯的时候,女生宿舍楼前,站满了依依不舍的恋人们,说着最后的绵绵的情话,久久地吻别着。
我和馨儿压低了头,默默地走在他们的中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我觉得脸有一点火辣辣的,尴尬极了。我微微抬起头,偷看了馨儿一眼,她的脸也红红的。
把车子停在宿舍楼前的车棚里,我鼓起勇气,拉了拉她的手说:“我下周再来找你。”
她的脸更红了,点点头。试了试,却没有抽回她的手。
我们的手轻轻地牵着,走到宿舍楼的门前。在灯光下和人前,我不由自主地松了松手。
馨儿马上抽回手,轻声对我说:“再见。”
我点点头,目送着她走进楼门。
她还是象上次一样回转身,向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很久,我没有离开。
我在想,我们在一起,如果周围有什么好笑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很开心地笑。可是,我们实在不象一对恋人,倒更象以前一样,还是朋友。
也许,下一次见她,我们应该呆在宿舍里,哪里也不去,只有我们两个人,象恋人一样,我应该吻住她,拥着她不放......
我的心一震,想起了馨儿娇好的身子。我拼命地捶了捶自己的头,努力地摆脱了那一丝绮念。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宿舍楼,灯刚刚熄灭了。我轻轻地说着:“馨儿,good night.”
回转过身,慢慢地走回车棚,慢慢地骑上车,慢慢地离开。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帮着花店的老板买了一台系里淘汰下来的IBM AT。 系里卖五千,我赚了五百的差价。然后,我又忙着帮他安装,调试。又教了老板怎么开机,关机和一些初步的使用常识。天天就在馨儿学校的附近,我却没有去找她。
我决定用那五百块钱,周末和馨儿一起去一家外滩边上的好西餐馆去吃一顿。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去找她是要给她一个惊喜。其实,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真的,起码不完全是真的。
这一次,也许是负疚感吧,我早早地来到馨儿的宿舍。她不在。我站在门口等着她,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么等着她,我的心里好受了一点。
她和两个舍友嘻嘻哈哈地端着脸盆从楼梯口走向寝室。她的头发还湿湿的,她们刚洗了澡回来。看着她潮红的面颊,黑湿的头发,纤细的身子。我的身体一热。我急忙站直了身体,看着她。
她看见是我,也是一楞,然后又回复平静。
她的两个舍友夹着她,促狭着她:“还不快点儿?人家可都等急了。”
“可不是。不过啊,我看汪馨她更急。”
馨儿本来想加快脚步,现在也不行了。她低着头,任她们说笑着。
她们一路慢慢地走过来。馨儿早早地掏出钥匙。到了门边,她没有看我,低着头,一只胳膊夹着脸盆,一只手去开门。
我看见她白皙的脖子,心中又是一荡。
也许是她在夹着脸盆,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她就是打不开门。
她的舍友笑着说:“喂,你还不帮帮汪馨?”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红着脸,接过了她的脸盆。
馨儿的脸也有一点儿红,她还是没有看我。幸好门一下子就打开了。
她的舍友拥着她走进去。
我举足无措地站在门边,端着她的脸盆。
她的舍友倒是很热情,召唤着我:“快请进。”
我挪进了门,还是端着脸盆,站在门边。
她的两个舍友忙着放脸盆收拾东西。
馨儿向我使了使眼色,我没有明白。
她只好说:“那边上面那个是我的脸盆架子,帮我放一下好吗?”
我转过头,帮她去放脸盆。
一个舍友开着玩笑:“哈,汪馨,现在已经开始使唤人家了?”
我的脸又一红。我忙放好脸盆,转过身,我看见馨儿也有些不自然。
另一个舍友马上打岔说:“汪馨,介绍一下吧?”
馨儿站起来,指着她的舍友们说:“ 这是范彤,比我们都大几个月,我们都叫她大姐。老照顾我们这些小妹妹。这是杨梅。我们都叫她扬眉剑出鞘,嘴特别的尖。”
杨梅笑骂着说:“有这么介绍人的吗?”
馨儿也笑了:“我还没说完呢!你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然后,她停了停,止住笑,看着我说:“他叫吴剑。我高中的同学。”
杨梅笑着说:“不仅仅是同学那么简单吧?上周末,我可是见你们拉过手的......”
范彤看见我和馨儿都有一点儿窘,忙插嘴说:“小杨梅,你就省两句吧。”
杨梅笑着说:“好,好,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范彤给我拿了张椅子坐下,看着我局促的样子,可能是想缓解一下气氛,笑着说:“我们这儿, 馨妹妹是最好,最有人缘的了。你可不许对她不好。”
我却更尴尬了,低下头,看着脚慢慢地划着地板。
杨梅接着说:“我们寝室的人商量好了,如果有哪个男的对我们姐妹不好,我们就人人共讨之,共诛之。”
杨梅讲话有一些南方口音,我不确定地问:“共逐之?”
她笑着说:“诛之,杀之。”
大家都笑了。
馨儿笑着走过来,对范彤和杨梅说:“你们就饶了他吧。”
然后,她把我推出寝室,说:“你先出去一下吧。我换一下衣服我们就走。”
杨梅笑着说:“呵,现在就护上了。”
寝室的门在我的身后关上,门内是小女儿的嘻笑打闹声。我拼命制止住自己去想里面的旖旎风光。
过了一会儿,馨儿笑着从宿舍里跑出来,她大叫着:“我怕了你们还不成?”把门关上。
门内传来范彤和杨梅格格的笑声。
馨儿又穿了她那一件最喜欢的黄色的连衣裙,衬着她白皙的肤色,显得格外的娇媚。她还在笑着,微微地娇喘着。我定定地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她止住笑,看见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探询地看着我。
我急忙掩饰自己说:“你要不要去加一件衣服?晚上可能会冷的。”
她一边摇摇头,一边向前走,说:“不会吧?我可不愿意再回寝室拿衣服了。我受不了她们的玩笑了。”
她说着,又微微地笑了。
我跟着她,问:“她们都开什么玩笑了。”
她笑着说:“还不是些女孩子间的玩笑。”她说着,止了止笑,脸有一点红。
我也有一点儿脸红。
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下了楼梯,出了她们的宿舍楼。
站在宿舍门口,她看了我一眼,问我:“今天我们去哪里?”
我说:“外滩的一个西餐馆,我订了位。”
她开玩笑说:“哇,每次都请我吃馆子,是不是要象填鸭似的填肥我啊?”
我脱口而出:“不是的,馨儿,你瘦了。”
我后悔地看着她。
馨儿一愣,慢慢地收住笑。
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又挂着淡淡的微笑说:“好啊,不吃白不吃。你是不是发财了?需要 订位的馆子都应该不便宜的。”
我得意地说:“还记得我上周跟你说那个花店老板要买电脑的事儿吗?”
馨儿点点头。
我继续说:“系里卖五千。我一转手给他加了五百的帽子。”
馨儿关心地问:“他你不是说那个老板挺精明的吗?他没有看你系里的发票吗?”
我回答说:“我随便用电脑打印了一页报价单,把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馨儿还是关切地说:“你小心点儿。还不如跟他挑明了是加收手续费的呢。”
我有点儿不耐烦地说:“好吧。下次吧。走不走啊,我可是饿了。”
馨儿有点儿歉疚地说:“不好意思。快走吧。”
我也不好意思了,笑着说:“我逗你的。说实在的,我现在也觉得还不如明说要收手续费或是介绍费之类的呢。好了,不说了,管他的,先享受一番再说吧。啊哟,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这个礼拜的免费玫瑰还没拿呢!”
“算了吧。先去吃吧,可不能把您老人家给饿着了!要不然,生起气来,可真吓人。”馨儿笑着说,说完就先跑向公共汽车站。
我也追上去,大叫:“哪儿跑!”
餐馆很别致古朴,是昔日上海租界留下来的哥特式的建筑。青苔和墙上修补的痕迹默默地诉说着它自己的历史。人并不多, 我们订到了楼上临窗的位子。
一进大门,一层镂空的大厅中间放着一架乳白色的三角钢琴。 木制的地板虽然有些陈旧,却很干净。 圆圆的小桌子, 洁白的桌布,幽幽的烛光,虽然稍微显得挤了一些,却也给人一种intimate(亲密)的感觉。侍应小姐引着我和馨儿拾级而上。红红的软软的地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们临窗坐下来。我鼓励馨儿点了一杯红酒,自己点了一杯矿泉水。我们执着高脚杯,轻轻地晃着酒杯,看着窗外。
黄浦江的难闻的味道被室内洒的香精的味道给压住了。在傍晚的余晖下,海鸥飞翔着,几艘小艇漂泊着,浓浓的 江水荡漾着, 映着日落和外滩边初上的霓虹灯。江边还依偎着一对对的恋人,晚风轻轻地吹拂着他们。
“黄浦江如果没有那股味道,也还不太丑。”我说。
馨儿啜了一口酒,点点头。
这个时候,楼下的钢琴声起,我们侧过头,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弹琴。音乐从她的指尖流畅地洋溢开来。看着她,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单颖,如果那算是女朋友的话。她也是学钢琴的。她充满了对钢琴和音乐的热爱。 我想,她是有天赋的,但不是有天才的那一种。她练得很勤奋。她也因此被提前一年录取进中央音乐学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请她去北京音乐厅边上的咖啡厅去喝咖啡。有一位她崇拜的中年女钢琴家去咖啡厅弹琴赚钱,被一群暴发户给搅和了。她为此而哭了。这个女孩子也应该是在上海音乐学院之类的学校念书吧?可惜,我听不出她弹得好还是不好。
我努力收回自己的目光和思绪。我看见馨儿把自己埋在菜单后面。我也急忙拿起我的菜单。 我有点想掩饰,笑着问她:“你点什么啊?可别替我省。”
她笑了笑,念着菜单上的英文说:“Chicken pasta. (鸡肉通心粉)。你呢?”
我念着英文说:“Surf and Turf.(牛排和虾)。”
她笑着说:“Steak again? (又吃牛排), 忘了我们上次在马克西姆吃的时候,你出的洋相啦?”
我也笑着说:“哪能忘了呢?我不过是不轻言放弃,屡败屡战而已。”
她笑了,然后,似乎陷入了回忆中。我也静静地回想着那一次温馨的回忆。
"Excuse me, we could not help but overhead you. You can speak English pretty well. (对不起,我们不小心听见了你们的谈话。你们的英语很棒啊。)”邻桌坐着一对美国老头和老太太。
我和馨儿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馨儿看了看他们,微笑着说:“Oh, thank you."
太太问我们:“College students? (上大学呢?)”
我回答说:“Yes, we just started our freshmen year. (是的,我们刚上一年级)"
先生问:“Which school?"
我回答道:“ I go to Fudan. She goes to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我上复旦,她上上海外国语学院。”
太太赞叹道:“No wonder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Both are top schools. (怪不得你们的英语这么好。两所学校都很棒)。”
先生又调皮地看了我们一眼,笑着问:“Are you couples? (你们是一对儿吗?)”
我们两个人都脸红了,低下头。我点了点头。
先生大笑起来:“Do not be shy. Been there, done that. When we were young, we used to be like you, we could just sit there, doing nothing, just watching each other in the eyes for hours. (别害羞。我们也这样过。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象你们一样,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只是互相看着。)”
我们更害羞了。把头压得更低。
老头笑得更欢畅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菜来了。太太止住老头,自己也笑着对我们说:“Do not pay attention to what he said. I do not. Well, enjoy your meal, and enjoy yourself. (别理他胡说八道的。我就懒得理他。好吧,好好享受你们的晚餐,享受你们自己。”
“Sure, you too.(好的,你们也是如此。)”我回答她。
我们急忙开始用餐。
我一边吃着,一边凑过到馨儿面前, 笑着说:“还记得我们以前看京戏的时候认识的那对外国夫妇吗?跟他们一样逗。”
馨儿压低了声音说:“你轻点儿,没准儿他们也象上次那一对夫妇似的,会讲中文, 就是不说, 听我们用中文讲了一大堆他们的坏话,最后才告诉我们。”
我点点头。
馨儿又用更低的声音说:“现在这对,更损。”
我们都笑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和馨儿有太多的过去可以回忆,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因此而过多地沉溺于过去,而不能重新开始。
外面有一声汽笛,一艘轮船缓缓地江面上驶过。
馨儿转过头,定定地看着那艘轮船,过了一会儿,她幽幽地感叹道:“不知道人生是不是也象这船和这江水,永远不会再一样,再重复,永远也不能再重新来过。也许,这轮船可能不久以后又会从这里经过,可是不要说轮船本身会变,会变旧,就是江水也永远不可能再一样了。”
我紧张地看着馨儿,猜测着她话里的意思。我小心翼翼地问她:“馨儿,你想说什么呢?”
馨儿转过脸,她的眼睛里噙着泪,她大声对我说:“木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你这样小心谨慎地刻意地要对我好, 我不要你这样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和我讲话,揣摩我话里的意思。我知道你想要我开心。可是你这样,我不开心。你不开心,我怎么能开心呢!”
这是馨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发脾气。我有点呆住了。周围的人也都看着我们。
馨儿伏在桌子上,哭起来。看着她瘦弱的肩膀随着啜泣耸动着,我的心好酸。我轻轻地抓起她放在桌子上的左手,紧紧地捏着。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馨儿又哭了一会儿, 抬起头,她把手翻过来,压住我的手,也紧紧地捏住,说:“木头,该我说对不起的。不好意思,这些天我好累。脾气大了些。你等等我,我去一下洗手间。”
我呆呆地看着馨儿离开,心乱如麻。
“Hi, we are leaving now. Is everything Ok over there? (我们要走了,你们没什么事儿吧?)”那位外国老头问我。
我出于礼貌回答他说:“We are fine.(我们没事!)”
“This is my business card. Hopefully, we can see each other sometimes.(这是我的名片,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见面。)”老头递给我他的名片。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HP CHINA Vice President. (惠普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 我忙说:“谢谢。”
他的太太走过来,对我说:“Cherish each other. Cherish what you have got. (珍惜彼此,珍惜你们所拥有的。)”
我看着他们诚挚的目光,点点头。
馨儿走回来,她洗了脸,已经恢复了常态。她看了一眼邻桌,问:“他们走了?”
“是的。老头还是中国惠普的副总裁。给了我一张名片。”我回答她。
“噢。”馨儿应了一声。她没有再说话。
一直到我们吃完饭,走出餐馆,我们都一直没有再说话。
一出大门,江边的夜风吹来,馨儿打了个寒颤。我脱下我的外套,给她披上。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问她:“馨儿,我们在江边坐一会儿,好吗?”
她微笑着问我:“你不嫌黄浦江的味道啦?”
我笑着说:“好象天凉了,味道也没有那么重了。”
她答应着:“好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揽过她。我们一起过马路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脚步还是怎么也不合拍。不是我慢就是她慢。我觉得,她也在象我一样,想调整自己的步伐来适应我。而这也正是我们的问题。
好不容易到了江边,我们找了一个椅子坐下。 馨儿把外套和我一起披上。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在泰山上,一起披着那件旧军大衣的时候。我的心中一阵温馨,我微微地侧过身来。她温顺地把头靠在我的怀里。我们很久都没有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拥着她,我却觉得那个时候,离得她更近。
过了一会儿, 她抬起头,我低下头,我们几乎是同时要说话:“木头...” “馨儿。”
我赶紧说:“你先说。”
她勉强笑了笑,说:“我只是想说,我想起了我们在泰顶时候的情景。你呢?”
我很高兴地说:“我也是。”
我揽过她。馨儿把她的头又靠回我的怀里,充满了憧憬地说:“我真的好怀念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快乐。”
她顿了一顿,犹豫了一下,然后,她抬起头,紧紧地看着我说:“木头,我们还象以前那样好吗?”
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着急地说:“馨儿,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她看了看我,苦涩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变得更加紧张,和不自然。我很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说:“再给我几次机会吧?”如果我又搞砸了怎么办,浪费了这最后的机会怎么办?
内心的不安让我觉得外面的一切都很别扭。我觉得我的外套太小了,我比馨儿高,我必须把自己滑下一点才能和她一起披着我的外套。呆久了,我觉得腰好痛好酸。我尽力地把衣服移向馨儿,自己却也有一点冷了。我的右手用一个固定的很不自然的姿势揽着馨儿,早就酸了累了。
可是,我不敢动,不敢说什么,也不敢说要走。
过了一会儿,还是馨儿看了我一眼,说:“我们走吧。天晚了。风更冷了。我们也都累了。”
我们站起来,馨儿非要把外套让给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衣服给她裹上,自己在前面跑起来,我回过头来, 大叫:“你也跑一跑吧,跑一跑就不冷了。”
馨儿也慢慢地跑起来。
正好我们要坐的公共汽车来了,我快跑几步,喘着气,扒住车门,等着馨儿。
馨儿加快了脚步跑过来。
我们两个人呼哧带喘地上了车。
馨儿买票的时候还不忘了谢谢售票员:“阿姨,谢谢您让司机等我们。”
售票员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不用谢。”
车子开了,我们摇摇晃晃地坐回我们的座位。很久没有在身体上这么累了。出了一身汗,却觉得挺痛快的。也许身体累了,头脑就不再费劲地去想东想西了,心也不再那么累了。
我们一路上坐着,好不容易才喘过气儿来,车就到站了。
下了车,我笑着问她:“还跑吗?”
馨儿点点头。
我们两个人一起向她的宿舍跑去。在她的宿舍楼前,我们停下来。
看着她娇小的身子包在我的外套里,我突然一阵冲动,我把她揽过来。我真的想就这么揽着她,什么也不做。 可是,我想起了我最后的机会。我吻上她的唇。她的唇是冰凉的,我的也是。我们努力了一会儿。馨儿慢慢离开我,她又挂上了那种淡淡的苦涩的微笑,她说:“太晚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我害怕极了,急忙问她:“我下周末还可以来找你吗?”
她看着我,点点头。
我高兴得跳起来。
她也笑了,把外套递还给我,大声说:“我得先跑回去了,太冷了。快成冰棍了。下周六再见。”
我一边看着她跑回宿舍,一边心里想着:“下一周,我又该怎样做才能不让她失望呢?”
我新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以后我的文章会在那里首发,欢迎扫码关注,非常感谢:

我的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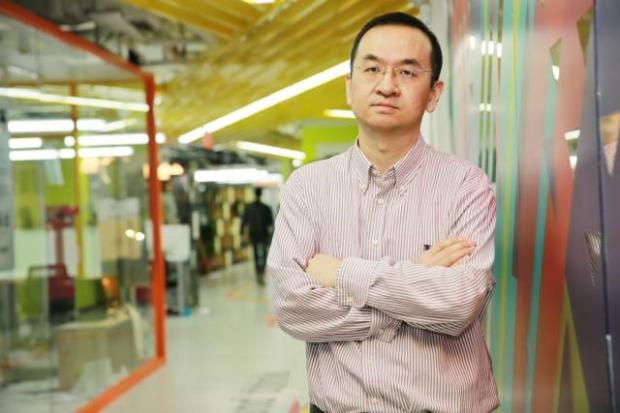
程励箭,自由而无用发起人, 互融资本创始合伙人, 主要从事创业孵化及天使投资,并任北京大学EMBA班兼职讲师,讲授创业辅导课。曾在美洲银行等华尔街金融公司工作。后在美国创业两次,一次为智能卡行业门户,一次为生物医学行业垂直网站,均成功出售退出。曾任IBM美国公司战略咨询高管,架构委员会成员,为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高盛,美林证券,沃尔玛,亚马逊,雅虎等提供战略,业务及技术咨询服务。曾任财经CTO。曾经负责华润集团电子商务,大数据,互联网等创新业务的拓展及独立分拆上市工作。任高伟达的副总经理,负责其创业板上市工作,并成功在创业板上市。后在国内创业,主业为互联网金融,P2P,众筹,成功出售退出。
目前关注人工智能,影视,相关博文:
《青春做伴》影视:
人工智能:http://chenglijian.blog.caixin.com/archives/168026
我的微信:leejcheng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